邓殿臣(1940-1996),中共党员,教授。1966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僧伽罗语专业毕业留校任教,曾任僧伽罗语班主任、僧伽罗语教研室主任、亚非语系总支书记、中国南亚学会理事、中国亚非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曾先后三次到斯里兰卡工作、研修,对南传佛教和斯里兰卡历史、语言文化有很高的造诣和成就,先后翻译6部南结大藏经佛典《长老偈》、《长老尼偈》、 《小诵》(含10部小经)、《即兴自说经》、《大隧道本生经•传》、《大念处经》。参与《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大百科全书•语言卷》、《南亚词典》、《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词典》、《东方现代文学史》、《东方思想宝库》、《世界名著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斯里兰卡部分的编撰,主编《东方神话》。
“清晨,六点还未到,我被电话惊醒。来电话的是邓殿臣先生的内弟。他向我通报身份后,不详的预兆便袭上我心头。但当他告诉我邓殿臣先生猝然去世的消息时,我仍然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家振《叹又弱一个,盼乘愿再来!》——悼邓殿臣先生)这是佛教文化研究学者家振先生接到邓先生逝去消息时的第一反应,他与邓殿臣先生结缘于《南传大藏经》。当时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开展了一个翻译《南传大藏经》的项目,此前虽然有从日文、英文转译过的部分《南传大藏经》,但是季羡林先生认为,转译容易造成背离原意,因此直接从巴利语翻译才能准确表达原典的内容。(巴利语是古代印度的一种俗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语族的一种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与梵语十分相近。这种语言如今仍然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方被保留跟使用着。)在当时那个极度稀缺懂巴利语人才的社会环境下,翻译《南传大藏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首先积极响应号召的便是邓殿臣先生,他不会做些虚情假意,碍于情面的事,而是真正发自内心,出自热枕。邓先生本人是学习僧伽罗语的,斯里兰卡当地人称他的僧伽罗语比当地人还要纯熟。为了响应研究所的项目号召,专程去斯里兰卡学习巴利语,又与北大的斯里兰卡留学僧威玛莱那坦尼学习,合作翻译了《长老尼偈》。家振先生表示曾看过他的学习笔记,下了不少苦功,他的学习能力和坚忍的毅力着实让人钦佩;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翻译项目,他还让自己的妻子去斯里兰卡学习佛教和巴利语,让儿子去中国佛学院听课,并去斯里兰卡学习。“为了这一任务他真正下了决心,一片志诚,苍天可鉴!”家振先生在悼文中这么写到。邓先生学成归来后,同众多志同道合的学者专家一同翻译了《南传大藏经》的5-7部。正当大家都信心大增,准备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项目进展前景一片大好之时,可能是天妒英才,也可能是因为过度劳累,天不假以余年,年仅56岁的邓先生就突然撒手西去了,徒留遗憾。

作为翻译《南传大藏经》项目的发起人,中国佛教领袖、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赵朴初先生听闻这一噩耗,十分惋惜。出于赞赏邓先生的奉献精神,赵朴老不顾卧病在床,亲手为邓先生题写挽联:“通声明而达内明,堪伤博学英才,又弱一个。 积世智以臻大智,所愿翻经妙手,乘愿再来。”赵朴老的大意是,邓殿臣先生是由翻译而入佛门的,他的外语知识本就是世间智慧,通过翻译佛经更加领悟了人世真谛,可惜这样的稀缺人才,又少了一位。家振先生在邓先生去世后,与他的家人孩子,以及多位合作过的学者专家进行过交谈,大家都表示会尽力实现邓先生的遗愿,齐心参与译经大业。生命长河不息,译经事业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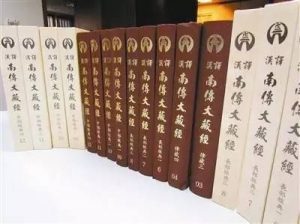
邓殿臣先生自1966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僧伽罗语专业毕业后便留校任教,兢兢业业栽培后学,为弘法利生,夜以继日,满腔热枕。一心传播佛教文化,填补学术空白,整日忙着开会、授课,风雨无阻关怀异国参访学生,竭尽所能为兰卡友人提供生活所需。邓先生安排好了身边所有的人事,却唯独没有自己的时间调养身体。“沉思良久,那古老的梦影、生命的真诚碰触与探寻,胸中翻腾着岁月的百千的情境,人生苦短,如幻如奇,缘起缘灭,周而复始,虽沉沦于人世的苦海酬偿宿尽,但那生命的慧炬仍常照心里!”(静涛《君且去 休回顾》——悼一位佛教学者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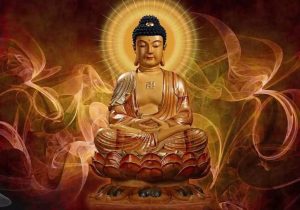
笔者钦佩这样一位将自己的一生几乎都奉献给了翻译和佛教事业的学者,祖国需要这样的智慧信徒,默默耕耘。邓先生的心愿是:“续四生的慧命,燃千圣之心灯”。所学所愿竟燃烧到四生四世,足以见邓先生的一片丹心。相比之下,笔者等普通人实在太过渺小,以下奉上邓先生《”巴利三藏”略说(节选)》以表纪念:
几种字体的“巴利三藏”和几种语言的译本
巴利语是一种发音响亮、声调优美和谐的语言,但它没有自己专用的字母,通行巴利语诸国,皆用本国母语的字母拼写。南传诸国及西方,也将“巴利三藏”译成了本族语言。下面介绍几种字体的“巴利三藏”和几种语言的译本。
僧伽罗字本:这是现有各种字体的“巴利三藏”中最为古老的一种。公元前1世纪,兰卡大寺500高僧举行大结集,把一向口口相传的“巴利三藏”记录在贝叶上的,使用的就是这种字体。这部僧伽罗字“巴利三藏”流传至今,基本上没有变动。到了现代,为纪念佛陀涅槃2500周年,斯里兰卡组织一批饱学长老、以兰卡大寺传本为依据,参考缅、泰诸国传本,从1954年开始对“巴利三藏”进行校订和译为僧伽罗语的工作(以前也有不少经文译为僧伽罗语,但不成系统)。历30余年,始完成此项事业,印出了新版的僧伽罗字巴利三藏和僧伽罗语译文的对照本,共52册。原斯里兰卡在华专家李拉拉特尼先生曾赠给中国佛协20余册。
泰字本:泰国一向对“巴利三藏”特别重视。最初,抄写“巴利三藏”使用的是柬埔寨字。到公元1888年,拉玛五世朱拉隆功(1868—1910)礼请王弟金刚智组织高僧,参考斯、缅诸本,对“巴利三藏”进行了修编,改柬字体为本国的泰文字体,历5年而成,编39册,印行100部。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完备的纸印“巴利三藏”。到拉玛七世(1925一1934)时,僧王斯里瓦德那在国王护持下,组织长老修订五世时的“巴利三藏”,于1926年完成。这套更加完备、更加精确的版本分45册(象征佛陀说法45年)。泰国目前使用的,仍是此本。1940年,僧王帝须提婆在政府赞助下,组织“巴利三藏全译委员会”,礼请几十位高僧,将“巴利三藏”全部译为泰语(在大城王朝和拉玛三世时期曾经译出过一些单品,但很不系统,很不精确)。历时12年,于1952年完成。这部泰语译本有律藏13册,经藏42册,论藏25册,合计80册(象征佛陀世寿80岁),印出2500部(象征佛灭2500周年)。1989年底,泰国议长将一部泰语三藏赠送中国佛牙塔,被中国视为一套珍贵的佛教文献。
缅字本:缅甸是一个南传佛教大国,其抄刻经文,翻译经书的事业更加宏伟。公元1871年,缅王敏东(1853一1878)礼请2400高僧,在都城曼德勒举行第五次结集,将以“律”为主的“巴利三藏”用缅字镌刻在729块方形大理石上,历5年而成,成为缅甸的一部“石经”。1954年,为迎接佛灭2500周年,缅甸发起第6次三藏结集,以曼德勒石经为依据,参考斯、泰、柬及巴利圣典会等各种版本,对“巴利三藏”详加校订,新出版了缅甸字体的“巴利三藏”。
柬字本:柬埔寨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初立“三藏委员会”,组织著名学昔校勘“巴利三藏”,同时开始译为柬语的工程,于1938年完成。柬文字体和柬译三藏合计110册,在柬埔寨各地流通。
傣字体:我国傣族地区所依的“巴利三藏”以傣语字母拼成。细分,又有傣泐文、傣纳文和傣绷文3种。三藏中的“相应部”和“增支部”中的大部分经文尚无傣译,其它诸经已译为傣语。傣地经书皆为手抄本,细分为贝叶本和纸写本两种。
罗马字及英译本:英国佛学家李斯·戴维斯夫妇于1881年成立“巴利圣典会”,出版罗马字体“巴利三藏”。不久,又陆续将“巴利三藏”全部译为英语,收在《东方圣书》和《佛教圣书》内。其中一些重要的经文,则是一译再译,出版各种选译本和节译本。如律藏《大品》、《小品》就有3种不同的英译,《法句》的英译本多达30多种。译为法、德诸语的单品也有20余种。
日译本:1935年至1941年,日本依据巴利圣典会的英译本,由高楠顺次郎监修,翻译出版了《南传大藏经》70册。除“三藏”之外,还收入了藏外的《弥兰陀问经》、《岛史》、《大史》、《清净道论》、《摄阿毗达摩义论》、《阿育王铭文》等。
汉译:与英译、日译相比,系统的汉译工作起步较晚,落后许多,至今仍仅有几篇零星的单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大的憾事。古代汉译诸经中,虽然有些与巴利经典“相当”(如“四阿含”),但并非译自兰卡大寺部的传本,而是译自其它部派的梵本或西域诸语,所以两者之间仍有区别,只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不应该笼统地说“某经同于某经”。
1943年成立的“上海普慧大藏经刊印会”本计划出版北传、南传全部经典,但计划未能实现,南传“巴利三藏”只从日译转译6册为汉。这6册是:江錬百译的《长部》2册,23经。沙门艺锋译的《中部》1册,前50经。夏丐尊译的《小部》2册,是“本生”中的“因缘总序”和前150个本生故事。范寄东译的《发趣论》1册。1981年,中国佛协叶均先生译出《清净道论》,1985年译出《摄阿毗达摩义论》,并重译《法句》(前两书为藏外巴利经典)。1985年,郭良鋆、黄宝生合译出《佛本生故事选》,选译本生故事154个。1990年,郭良鋆译出《经集》。这些汉译加在一起,仍仅占“巴利三藏”极一小的一部分。
近几年来,台湾“异军突起”,元亨寺成立“南传大藏经编译委员会”,在吴老择先生主持下,从1988年开始进行系统地汉译。现已译出40余卷,将依律、相应、中部、长部、增支部、小部、论部、史部的次第陆续出版流通。他们仍采用自日译本转译为汉的办法,但初稿要送斯里兰卡,请法光法师审定。法光法师精于南北两方佛教,通晓巴、梵、英、汉、僧伽罗数种语言,由他“把关”,可保证译文的质量。(摘自《”巴利三藏”略说》)
参考文献:
【1】家振. 叹又弱一个,盼乘愿再来——悼邓殿臣先生. 佛教文化.1996.6
【2】静涛. 君且去 休回顾 ——悼一位佛教学者之死. 佛教文化. 1996.6
【3】邓殿臣. “巴利三藏”略说. 佛教文化. 1991.3
作者:唐颖